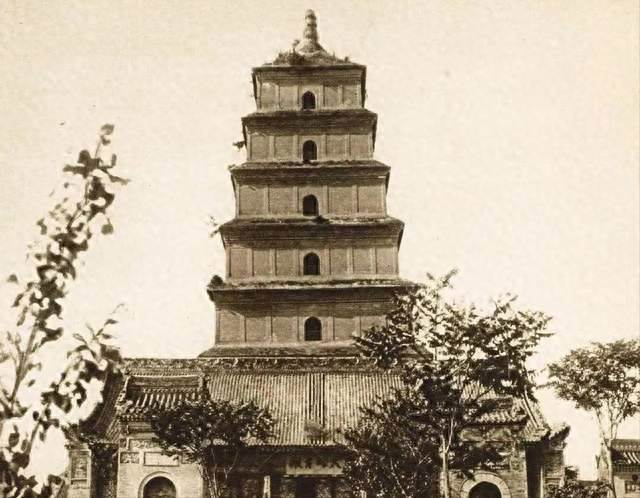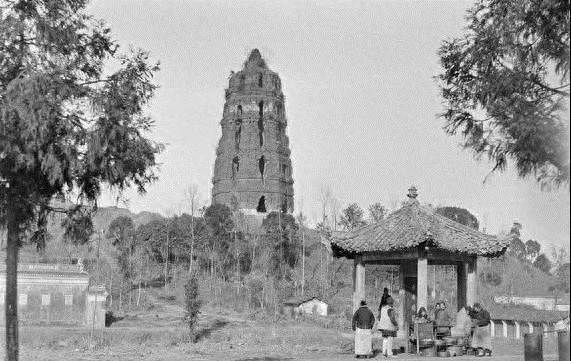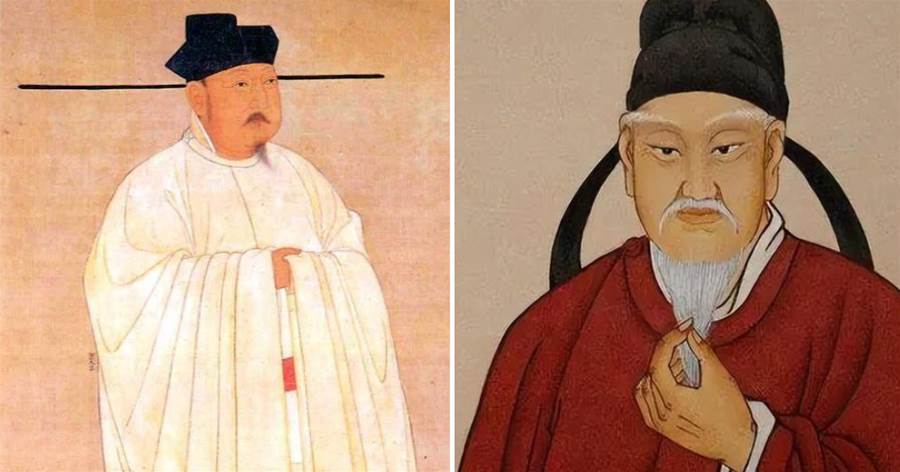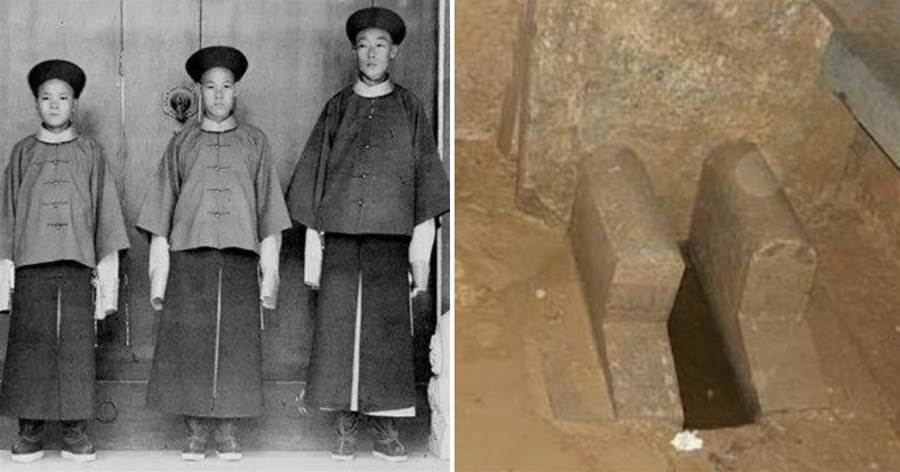2002年,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,考古發現一把奇怪的「木胎漆繪圭尺」:殘長171.8厘米,復原長度187.5厘米,圭尺上由間隔黑色和綠色格間以紅色道標出刻度,其中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,從頭端到此刻度39.9厘米。

該圭尺具體出土的地點,是在遺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。其中,「大型元首墓」比一般的王族墓地還要大,說明墓主在位時國力尤其強大;同時,說明該圭尺對墓主極為重要,因為「事死如事生」,故而將之陪葬。
陶寺遺址時間跨度為距今4300—3900年,中期大概是4100年。在中國史書上,這一時期最有名的帝王是堯舜。由于圭尺是立表測影、觀象授時所用,而《尚書·堯典》中有帝堯「分至四神」、測得「歲三百六十六日,以閏月正四時」等。
除此之外,還有陶寺朱書陶文、觀象台等,種種線索都表明圭尺主人應是帝堯!
問題在于:帝堯為何突出圭尺的第11格刻度,背后到底有何意義?以先秦文獻記載看,至少表達了兩層重要含義。

尚書堯典記載,帝堯派四個官員分駐四方,以確定中春、中夏、中秋、中冬,其實就是二分二至,四個官員就是「四神」,合起來即「分至四神」。但談到代表南方的夏至時卻說「平秩南訛,敬致」,其他三方都沒有「敬致」,為何偏偏如此禮敬夏至?陶寺圭尺印證了這一記載。
上古時期,立表測影是觀象授時的重要手段,即根據正午影長判斷節氣。具體來說,就是豎立一根「表」,橫放圭尺,正午陽光照射,表影在圭尺上「勾」出影子長度,以此判斷節氣。
現代學者研究發現,陶寺出土的圭尺刻度,對應了20個節氣,其中包括二分二至,即當時古人將一年劃分為20個節氣,與后世的24節氣不同。更為重要的是,陶寺觀象台也可以觀測到20個節氣,再度證明陶寺先民是將一年劃分為20節氣。

對于特殊的第11格刻度,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駑指出:按照一尺25厘米計算,39.9厘米的長度,說明第11格刻度的長度近乎1.6尺,與《周髀算經》記載的夏至日影「一尺六寸」長度相同。實際立表測影也表明,這一刻度對應的是夏至正午日影長度!
顯然,帝堯「敬致」夏至,而陶寺圭尺又特別突出夏至這一刻度,兩者之間無疑存在因果關系。學者馮時推測,帝堯「敬致」夏至的原因,應與古人認為「南方象天」、即天國在南方有關,故而古人坐北朝南,城市皇宮位于北邊、坐望南邊等。

周禮記載:「地中,天地之所合也,四時之所交也,風雨之所會也,陽陰之所合也,然則百物阜安,乃建王國焉。」在古人眼里,既然大地是方形的,自然就該有地之中央。當「國家」與「地中」結合之后,就形成了「中央之國」——中國的概念。
根據文獻記載,中國「地中」在夏朝時期出現過一次變遷:周禮記載「日至之景,尺有五寸,謂之地中」,地中在如今的河南嵩山告成鎮。但此前的地中,周髀算經記載「周髀長八尺,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」,恰好就在陶寺遺址,準確的說是在陶寺遺址所在的緯度線。
清華簡記載帝堯派舜測中、以及「舜既得中」,這與論語中的帝堯禪位時告誡帝舜「天之歷數在爾躬,允執其中」可以互相印證。
夏朝時期,商族先公上甲微「測影追中」,確定嵩山為地中。

因此,陶寺遺址出土的圭尺,特意突出第11格刻度,強調夏至這一刻度,顯然也有「地中」概念,即認為陶寺在地之中央,是為中央之國!正因如此,如今學者才會稱陶寺遺址為「最初的中國」。反過來說,陶寺圭尺也再一次印證了中國史書記載。
令人費解的是,位于河南濮陽的西水坡遺址,距今6500年,已經掌握「分至四神」、蓋天說宇宙模型、28星宿、立表測影等,是史前又一個天文極其發達的聚落,但該遺址位于北緯35°44′50″,而陶寺遺址位于北緯35度52分,兩者夏至日影長度近乎一致,那麼這兩座相隔2000多年的遺址有沒有聯系,或者是不是刻意選擇夏至日影「一尺六寸」的陶寺之地?

關于本文話題,還有兩點值得思考:
首先,文明是逐漸發展演化積累而來的,必會經歷循序漸進的客觀過程,必會留下相應演化痕跡。「中國」之稱、「坐北朝南」傳統等等,都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,如今考古都可以發現源頭痕跡。因此可以說,中華文明是一部連綿不絕、循序漸進、客觀真實的原生文明。
其次,史書上的帝堯歷史,既真實又不真實。不真實在于,后人將很多先人成果歸于帝堯,比如分至四神、對夏至敬致在西水坡遺址中已經出現,這與黃帝等發明很多成果一樣;真實在于,史書對帝堯的描述,的確能得到考古的一次又一次印證。
因此,西方學者提出「中華文明西來說」、否認中國史書可信度、否認堯舜禹夏朝等,其實原因很簡單,即不是蠢就是壞。
參考資料: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周髀算經》、《何駑——陶寺考古初顯堯舜時代的「天下觀」》等
嚴禁無授權轉載,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。